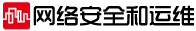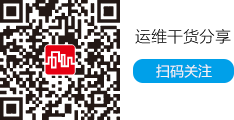網民們對互聯網企業信任的丟失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損失———
現在的情況是,被反流氓軟件稱為流氓軟件的不承認自己是流氓軟件,而反流氓軟件又被認為是“更大的流氓”。
流氓軟件,無疑是2006年互聯網行業最具影響力的話題。
12月22日,某機構公布了“2006中國IT產業之最”年度調查,在“IT產業之最”調查中,4項大獎無不與“流氓軟件”息息相關———“流氓軟件”以壓倒性優勢當選“2006年度最熱關鍵詞”及“2006最令人失望IT產品、服務”,而“反流氓軟件”則被評為“最應該被記住的年度標志性事件”,反流氓軟件聯盟發起人董海平,則力壓眾IT明星,成為網友心目中“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”。
所謂“流氓軟件”,也被稱為惡意軟件,根據中國互聯網協會的定義,流氓軟件是“在未明確提示用戶或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,在用戶計算機或其他終端上安裝運行,侵害用戶合法權益的軟件,但不包含我國法律法規規定的計算機病毒”。惡意軟件的惡行包括強制安裝、難以卸載、瀏覽器劫持、廣告彈出、惡意收集用戶信息、惡意卸載、惡意捆綁等。
問題是誰是“流氓軟件”。現在的情況是,被反流氓軟件稱為流氓軟件的不承認自己是流氓軟件,而反流氓軟件又被認為是“更大的流氓”,瞧這亂的。
官司判了,流氓未絕
12月20日,“雅虎訴奇虎不正當競爭案”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一審宣判,判決原告雅虎中國勝訴,被告運營奇虎網的北京三際無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(簡稱奇虎公司)將雅虎助手列為惡意軟件的行為,違反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》,對雅虎中國構成侵權,奇虎應立即停止侵害、賠償雅虎7萬余元,在奇虎網站公開賠禮道歉24小時。奇虎表示將上訴,兩虎之間的筆墨官司也仍然沒完沒了。
奇虎和雅虎圍繞流氓軟件進行的爭吵和訴訟,是今年互聯網行業最熱鬧的一出“戲”。年初,奇虎公司推出安全類軟件“360安全衛士”,將包括雅虎公司“雅虎助手”在內的上百款網絡工具類軟件列為惡意軟件進行查殺,隨后兩公司爆發了口水戰,從互指流氓上升到人身攻擊。多虧了它們吵開來,諸多潛規則才得以暴露在陽光下,困擾網民多年的痼疾,終于引起了廣泛的重視。前有反流氓軟件聯盟揭竿而起,后有中國互聯網協會以權威第三方的立場,公布《惡意軟件定義(征求意見稿)》,列出惡意軟件的八種特征。
但從兩虎案的判決中可以看到,中國互聯網協會的定義并未被法庭采納。如果沒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出臺,不能把惡意軟件散布者繩之以法,規范互聯網使用環境,就無法保護弱勢群體———普通網民的利益。
一位曾從事流氓軟件推廣的人士透露,現在為害更烈的是更加隱蔽的小插件。這種暗藏在網頁和下載物里的小程序,甚至開始廣泛采用病毒技術,如my123使用了驅動隱藏,7379使用了感染技術,3448采用了隨機名,Roogoo采用了LSP劫持技術等。它們會感染計算機上的可執行文件,傳播能力超強,具有極強的變身能力,不知不覺間損害網民利益。小插件泛濫成災,絕非散兵游勇所能做到,背后有著很強的技術和推廣能力,很有可能是大廠商在操縱,牟求商業利益。
“耍流氓”,賺快錢
流氓軟件的蔓延遠超出我們的想象:今年7月瑞星發布的《互聯網安全報告》顯示,過去6個月,流氓軟件侵害用戶的數量已在歷史上第一次超過病毒;一項網上調查顯示,99%的網民都受到過流氓軟件的騷擾;另一項調查的結果是,全球每臺電腦平均感染了24.5個間諜軟件,間諜軟件還只是流氓軟件的一種……
馬克思說過:為了300%的利潤,資本家連掉腦袋的事都敢做。管理學大師彼得·德魯克也說過:即使換了天使當CEO,他也要變著法去賺錢。所以,很好理解,“耍流氓”為了什么?一個字———“錢”!奇虎公司總裁齊向東估算,目前流氓軟件產業已形成10億元的市場規模,而且還在增長。
龐大的且不斷擴張的市場規模來自完整的產業鏈。目前流氓軟件主要靠兩個途徑盈利,一是安裝,二是廣告,買單的是廣告商。據一些從業人員透露,流氓軟件每成功在一臺電腦“安家”,廣告商就會為此支付一定的費用,流氓軟件侵占的電腦越多,其“價值”就越大,跟廣告商的要價就越高。之后,用戶上網時,每次通過該流氓軟件彈出廣告,廣告商也要按次付費。“一些大的企業月收入可超千萬元,有的甚至能達到3000萬元。”
這里面買單的廣告商不乏一些網站,他們借助流氓軟件,為的是提高點擊率。如此一來,表面上某些網站人氣非常旺,報表十分搶眼,投資商、廣告商趨之若鶩,實則背后是個空洞。
用流氓軟件推廣廣告或進行其他小動作,優點顯而易見:對雙方來說成本都很低,甚至為零;見效快,彈出廣告還具備分類識別功能,會更有針對性地在目標客戶面前彈出;不用承擔風險責任,至少目前是這樣的。有那么多企業不顧自己的形象可能受損而借助流氓軟件打開市場,足以說明其受歡迎程度。
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,流氓軟件賺來的快錢都“見不得光”,都是建立在損害網民利益、損害網絡環境的基礎之上的。如果說,“耍流氓”賺來的錢不管多少都還有個數字的話,那么,它對網民利益的侵害、對網絡環境造成的侵害(比如網絡安全隱患等)則無法用數字來衡量。而網民們對互聯網企業信任的丟失更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損失。
真空的不僅僅是法律
同情奇虎的一方觀點認為,奇虎之所以敗訴是由于相關法律法規缺位,法院雖然認定雅虎助手確實存在“難以卸載、強制安裝、干擾其他軟件運行和劫持瀏覽器”的行為,但是現有法律并不能判定存在這種行為的軟件就是惡意軟件。那些傳播插件的網站也可以振振有辭:法律沒有禁止進行插件廣告。
法律滯后并不是什么特殊現象,新行業新現象,法律法規必然是在實踐推動下不斷完善的。從流氓軟件現象中引發的更值得憂慮的真空,是P2P時代的責任人缺位。
P2P本意是點對點傳輸,在P2P時代,互聯網上大家都是平等的,沒有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傳播者,每個人既是互聯網內容的消費者也是生產者。這的確是一場革命,但絕不能對此太過理想化。每個人都是主人,有可能每個人都煥發主人翁的熱忱,也有可能每個人都不想負責,而且,人們并沒有能力完全為自己的言行負責。假如網民共同編撰的“維基百科”某些錯誤解釋誤導了使用者,共同開發的善意免費軟件導致了安裝者電腦崩潰,根本不知道該怪誰。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說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中,漆黑的夜里,12個兇手用同一把匕首,輪流刺了被害者一刀,究竟是誰的一刀致命,無從判斷。P2P時代的責任人缺位與此類似,網絡上一條假信息的制造和散布,一個流氓軟件的編制和傳播,當責任人數以億計,法不責眾就成了事實上的不得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