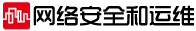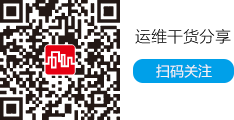中國這個社會很有意思,不管是哪次浪潮來了,“社”這個詞都是跟潮流捆綁在一起的社會和商業(yè)一體化組織。在第一次浪潮中,社這個詞跟農(nóng)業(yè)捆綁,是指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動。如魯迅筆下的《社戲》。在魯迅家南邊二百多米談過一場“錯錯錯、莫莫莫”戀愛的陸游,曾有“太平處處是優(yōu)場,社日兒童喜欲狂”的詩句。社在古代中國,作為一種組織,是不分層的扁平化組織。
在第二次浪潮中,人民公“社”成了中國的時尚。但這個社,已經(jīng)成了分層組織,分了三層,公社、大隊、生產(chǎn)隊三級所有。這與公社這個詞的法國含義,已有了很大差別。美國學者穆罕默德·塔巴克把巴黎公社當作人類第一個后現(xiàn)代的扁平化組織。初聽意料之外,細想情理之中:巴黎公社還真是個不分層的扁平組織。此公社移到了中國從扁平化結(jié)構(gòu)改成金字塔結(jié)構(gòu)了,顯然是因為工業(yè)化要求組織分層之故。
在第三次浪潮中,網(wǎng)絡“社”區(qū),又帶了一個社字。與魯迅的社、人民公社一樣繼續(xù)引領(lǐng)潮流。這回社回到了它的正宗,又變回成扁平化組織了。
中國一部“社”的史,就是扁平——分層——再扁平的否定之否定史。這是講區(qū)別。
社的一個重大特點,是社會活動和經(jīng)濟活動融為一體。無論農(nóng)業(yè)社會的社,工業(yè)社會的社,還是信息社會的社,都具有社會與經(jīng)濟的雙重功能。這是講它們相通的方面。
從這個意義推論,未來的網(wǎng)絡社區(qū),一定是電子商務與電子政務不分的,因為什么是公共物品,什么是私人物品,在社區(qū)事務中的區(qū)分越來越模糊,所以商務即政務。這可以說是網(wǎng)絡社區(qū)對社會和經(jīng)濟影響的一個重要特點。
網(wǎng)絡社區(qū),它既不是市場,也不是政府,而是介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東西。它要求一種不同于市場和政府的治理模式。事實上,治理這個詞本身在公共管理中的本義,就是指介于市場和政府(統(tǒng)治)之間的組織方式。但自克林頓、布萊爾以來西方社會的治理探索中,治理,或者說用網(wǎng)絡社區(qū)組織社會的模式,一直沒有穩(wěn)定下來。
法國和加拿大人把取經(jīng)的目標投向了中國,他們發(fā)現(xiàn)了未來網(wǎng)絡社區(qū)一個最理想的后現(xiàn)代先鋒派仿模對象:中國居委會的老大媽模式。居委會老大媽的后現(xiàn)代性質(zhì),據(jù)他們分析,主要體現(xiàn)在兩點:第一,她們是個性化服務(比如給夫妻勸架,總是一家一套說辭,以勸和諧為準);第二她們是不依賴稅收的(居委會不算一級政府,靠社區(qū)開店或服務為生,將來要靠社區(qū)電子商務)。兩者加起來,就是低成本的社會和諧,成為和諧社會的微觀基礎(chǔ)。
本來,西方后現(xiàn)代們發(fā)愁的是,個性化電子政務是要以高昂的成本為代價,最終受困于政府財政。中國老大媽用不花納稅人的錢提供個性化公共服務的光輝典范,給他們開了竅。網(wǎng)絡社區(qū)與居委會制度肯定會有巨大不同,比如,坐在那里的不是老大媽,而是一個整天照鏡子抹紅唇的畢業(yè)女大學生或什么版主。不確定的是,老大媽提供個性化服務的動力,是愛管閑事,尤其關(guān)心張家長、李家短的隱私。新一代在服務興趣方面,面臨新的問題。
中國現(xiàn)實社區(qū)在長達幾十年時間內(nèi),能穩(wěn)定地不靠稅收提供個性化服務的路子,為網(wǎng)絡社區(qū)提供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(jīng)驗。
網(wǎng)絡社區(qū)介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性質(zhì)決定了,它既不能完全是電子商務的,也不能完全是電子政務的,而須是在商業(yè)服務和公共服務之間找到一種公益性的平衡,同時在經(jīng)濟和社會兩方面提供個性化服務。這是21世紀的超級難題。這也是和諧社會要面對的問題。